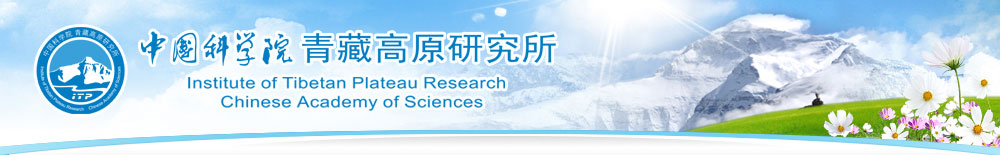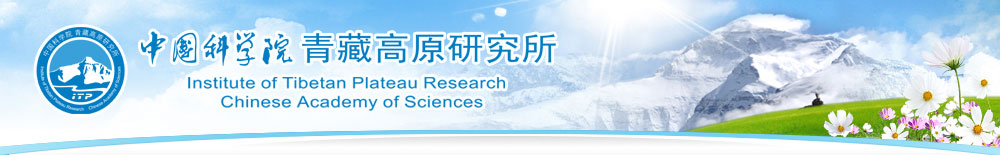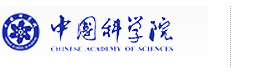《中外对话·Chinadialogue》-中国与世界,环境危机大家谈
朗尼•汤普森是冰核钻探领域的开拓者,也是研究喜马拉雅冰川的专家。这次,他接受伊莎贝尔•希尔顿的采访,阐述了在青藏高原研究方面科学超越国界的重要性。
朗尼·汤普森教授,世界顶尖古生物气象学家之一,高海拔冰核钻探领头人。汤普森读研究生的时候,冰川科学只关注两极地区,但他并没有被流行的观点所左右,坚信热带高山冰川的冰核可能蕴含着更多世界气候历史的信息。从那时起,汤普森从全世界收集高海拔冰川样本,他还是第一个在喜马拉雅山冰川进行钻探的科学家。这次,汤普森接受中外对话主编伊莎贝尔·希尔顿的采访,谈到转换思路的风险和回报,以及他在西藏的经历。
朗尼·汤普森(以下简称汤):我们的研究实在才刚刚开了一点头儿,反对的观点层出不穷,但也正因为如此才令人兴奋。科学的历史是通过范式转变而变化的,重大的突破总是来自某个人观察世界的新视角。就拿伽利略来说,他算出地球是圆的,而其他人认为是平的,以至于他被欧洲各个教会视为眼中钉。地平协会是最古老的学会之一,成立于1557年,其使命就是证明伽利略的错误。直到今天,我们已经发射了无数颗绕地卫星,但这个协会仍然存在,它根本就不理会什么证据。
伊莎贝尔·希尔顿(以下简称希):对新的科学观点来说,既有权威是不是一个特殊的问题?
汤:是的,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如果你成功了,人们就会觉得你的观点比别人的更有分量,特别是与年轻人相比。我是从极地研究入门的,但我发现当时热带高山冰川还是无人问津的一片空白,而极地研究的人们已经挤得不可开交。当我转入热带高山冰川领域时,有人警告我这会毁了我的研究生涯,要花很长时间才能挽回。我的一位同事说过,科学进步的同时就会有一个老的学说被埋葬,这非常真实。因此,每次年轻人提出新观点,就算我并不认为有什么了不起,我也非常努力地去鼓励。我一直铭记着一个事实:我们不可能无所不知,也永远不会知道下一个伟大的思想从哪里出现。
地球表面积一半在北纬30度和南纬30度之间,全球70%的人口居住在热带和亚热带。如果我们想改变地球的气候,那么就在热带和亚热带采取措施吧。厄尔尼诺之所以影响全球气候,是因为它在两个半球都发挥作用。
如果阿拉斯加发生一次大的火山喷发,受到影响的只是北极。但如果换到印尼,就会产生全球性的影响。因此,我认为地球气候大的驱动力量都来自热带和亚热带。我们都知道,欧洲和美国东海岸的科学最发达,所以大量的气候数据都是关于格陵兰岛和北大西洋。广大的热带地区则鞭长莫及,我们很难找到数据。
青藏高原也是如此。我们在那里的工作开始于1980年代中期,当时对这个地区根本一无所知。因为之前一直不允许外国人进入,我们甚至不确定那里是不是有冰盖。直到中美关系正常化,我们才得以进入青藏高原。但早在那之前我就给中科院兰州冰川冻土沙漠研究所的施雅风所长写信,我们1978年在堪培拉见过面,讨论了在冰原钻探的可能性。
希:在1978年的时候,你是否意识到这个地区对于气候变化的重要性?
汤:还没有。七十年代末,学界讨论的主题是下一个冰河期,我们的主要目的是把南极、格陵兰的历史和南北极之间地区(包括热带、亚热带和西藏)的联系起来,得到一个全球图景。两极的数据一直被当做全球气候的指标,但实际上根本不是那么回事。要知道,极地是没有季风和厄尔尼诺的。这也是我们开创新领域的初衷。
于是我们开始拍摄照片,一到两年更新一次地图。如果你得到一个数据点并且开始把结果绘在图上,就会发现冰川不仅在退缩,而且是在加速退缩。一些冰川现在的退缩速度是我研究开始时的10倍。这很惊人
在当时的西藏,主要问题是装备上的:怎样才能完成工作?怎样才能找到合适的人、得到许可以及其它一切有利因素,把冰核完好地用二战前的老爷卡车运出西藏?第一次进藏,我自己待了整整三个月,不会说藏语,其中有6个星期都是在天山的崇山峻岭里跋涉。我会和当时还在念研究生的姚檀栋一起走很远的路,一边讨论着科学和未来。但当时我们两个谁都想不到后来的结果会怎么样。
我还记得当时和姚檀栋及其妻女在兰州吃过的那顿拉面。那是一家小饭馆,连厕所都没有,还点着煤油灯。现在姚檀栋已经是中科院青藏高原研究所的所长,他们所在北京,刚刚又在拉萨建了一个新的办公地点。这一切都发端于中国荒凉西部的一个很小的念头。在首次进藏的后一个半月,我去了祁连山脉,找到了敦德冰川,那是我在青藏高原第一个钻探地点。
希:关于喜马拉雅冰川的情况,我们现在都知道些什么呢?
汤:我们刚刚分析完从喜马拉雅山脉西南部钻探出的冰核。那里是恒河、印度河和雅鲁藏布江的源头,海拔6000米,有冰原存在。2006年,我们在那里钻了三个冰核,一直钻到基岩,最深处达到158米。我们在这些冰核里首先要找的就是过去所有大气层核试验留下的痕迹。这些试验在全球各地都留下了放射物质层,在每个冰川内都能发现。我们之前在西藏的四个钻探地点都发现了苏联1962-63年大气层核试验的痕迹,这是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试验,留下了厚厚的放射物质层。但是,刚刚完成的冰核分析却没有发现它们的踪影。
我们也寻找着更早的美国核试验的痕迹。这一系列试验始于1951年,都在南太平洋,独特之处在于它们都是在海平面上进行的,因而产生一种放射性的氯。当时人们还没有意识到这些核试验有多么危险。这种氯-36能散布到全世界,从乞力马扎罗山的冰原,到安第斯山和西藏,处处都有它的身影。但是,在这次的分析中我们却没有发现它,这告诉我们,至少从1950年代末开始的净累积已经不在了。
从其他实验里,我们知道了第一层放射性物质形成于1946-1947年的试验。换句话说,海拔6000米的冰原从表面开始流失。每一个冰川都必须有一个堆积带和消融带,因此这些冰川都被削去了脑袋。2000年,我们在非洲的乞力马扎罗山竖起了标尺,迄今的测量结果说明山顶最高处的冰川表面已经失去了厚达2.5米的固体冰层。这些冰川也被削掉了脑袋,也就是说,融化的速度说明它们可能消失,以冰川融水为源头的供水受的影响会大大增加。
目前在西藏必须切实做到的事情之一就是确定这种现象的范围到底有多大。我估计,1987年我们钻探的敦德冰川的表层现在应该已经开始消融了,因为它的高度只有5300米。我们必须确定从表面开始消融的冰川的规模,还要确定什么高度的冰川仍然在累积,这非常重要。
希:还有冰川在积累吗?
汤:我确信还有一些。我们在喜马拉雅山最高的钻探地点是7200米,1997年进行的。那里的积累量大约是每年1200毫米,因为当地的季风气候非常明显。我估计,因为这个高度更寒冷,冰川仍然在积累。但是随着地球变暖,这个融雪线估计也会越来越高,而且由于更多的山峰达不到这个高度,那里的冰川量更大,消融量也就更大。冰川的消融,让千百万住在大河两岸的人们深受影响。
我们的模型解释了从低海拔开始自下而上的冰川消融,但我们在这里看到的冰川消融却是从自上而下的,因此变化会来得更快。这些冰川正在濒临消亡。冰川的定义就是运动中的积冰,如果没有积累,运动就失去了动力,因此它们只有坐以待毙。我们必须确定这种现象的规模,确定过去是否发生过。
我们在西藏已经做了很多研究,但要真正弄清楚这个系统,还有更多的事情要做。地球变暖影响着永冻层,许多人都关注草地的变化。随着永冻层的融解,表层的水分将会流失。草地会怎么样?人们的谋生能力会怎么样?你在动物园里没见过牦牛吧,这是因为进化决定它们只能生活在高海拔地区,海拔低了就会受到细菌病毒的侵袭。冰川和气候的变化对牦牛们会有什么影响呢?我相信还是有一些积极影响的,比如在更高的牧场放牧的能力。任何变化面前都有失败者和胜利者,但问题在于人们都聚居在条件较好的地方,条件变化了,他们就只能搬家。
发展导致许多煤烟进入大气,从而产生辐射反馈。那越来越多的煤烟会不会改变冰川的反照率,让它们融化得更快呢?现在还有很多未知因素。
希:从太空来看,青藏高原是一个单独的地理区域,但是回到地球上那里是有国境线的,过去有过冲突,紧张依然存在。那里的科学合作到什么程度,面临着什么障碍呢?
汤:我常常为自己是一名科学家而感到庆幸,因为科学家们认识到我们所研究的过程是不受国界限制的。我想我们之所以能在那么早的时候就进入中国,就是因为我们的职业:我们不推销任何东西,也不会从自己的工作中谋取任何利益。我们感兴趣的只是记录中呈现的问题:过去发生过什么,未来会发生什么?要回答这些问题,我们必须跨境进行工作,科学家们知道冰川不会因为国界而止步,但情况的改变需要时间。我第一次来中国去天山山脉考察时,有关方面给了我一张地图,划了条线告诉我哪里可以去。于是,即使冰川越过山口到了山脊的另一边,我也不能过去。
希:就因为你是外国人?
汤:是的,我是第一位走进中国西藏的美国科学家。
希:要进行这项非常危险的科学研究,你必须同时具备登山技巧和科学素质,或许这有一点疯狂。在大多数国家,遇到这种情况,二者兼具的人很难找到。现在情况有变化吗?
汤:我想这种兼具的人是很少见的。我们有很多研究生都希望加入到项目中来,因为他们想爬山。我一般不会收单纯的登山者当学生。对我来说,科学永远都是第一位的。我不是那种把周末登山当成休闲活动的人,因为那既危险又不舒服。
希:是根据工作的难度和冰川的数量来判断的吗?能不能用遥感和卫星来代替数据呢?
汤:遥感和卫星当然有用,但永远没有什么能取代数据。模型之所以伟大,因为它提出了大量的观点,对你拥有数据的记录进行解释。卫星通过演算法得到数据,但你必须用地面数据去解读。我们在乞力马扎罗山钻探到冰核记录,根据其在过去一百年中的活动情况,对这些冰原可能消失的年代进行了推演。模型专家们发表论文说,冰川活动和当今的气候是近平衡的,但就在他们拍摄照片的八年之后,那些冰川就消失殆尽了。真正能反映现实的,不是模型,而是数据和观测。
西藏幅员辽阔,因此你必须从不同地区得到非常精确的数据才能解读卫星照片。它们是相辅相成的。模型并非现实,现实来自对现实世界的测量数据。我认为科学就应该这样。有很多人整天坐在电脑前面,埋头建立模型,在卫星照片上测算着什么。我们当然需要这样的人,但他们也必须走出去进行田野工作。在我的实验室里,如果你是从事化学性质、尘埃或同位素计量的人员,至少要参加一次野外考察,因为你必须对计量对象的环境有所了解。你还必须懂得这些样本来得多么艰难,多么珍贵。而做到这一点唯一的办法就是你亲自走出去体验。
伊莎贝尔·希尔顿,“中外对话”主编。
朗尼·汤普森,古生物气象学家,任教于俄亥俄州立大学地球科学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