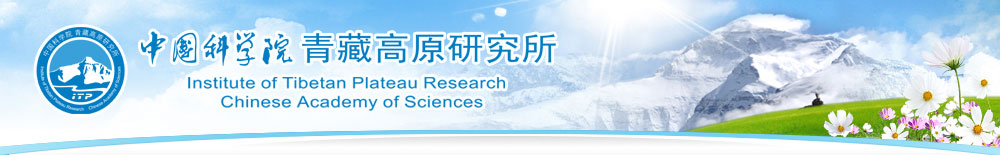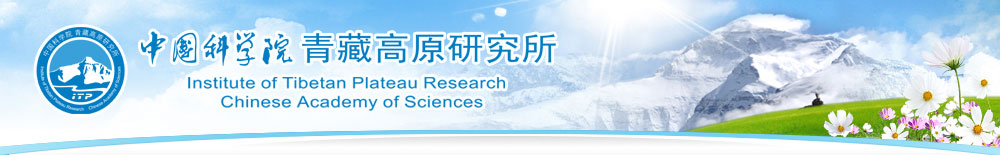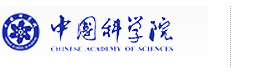摘自:基金委简报
编者按:著名科学家、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李政道教授近期专门撰文,回顾了他建议和帮助建立中国科学基金制的历史沿革,分析了现代科学发展的趋势,建议中国政府继续重视和加强基础研究,加大对科学基金的投入,更好地发挥科学基金制的作用,把握新的科学机遇,迎接新一轮科学革命的挑战。
上世纪80年代初期,中国实施改革开放政策,全面推行经济、教育、科技体制改革,消除“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消极影响。全国科学大会的召开,迎来了“科学的春天”。然而在遭受“文化大革命”破坏极为严重的基础研究领域,拨乱反正的任务依然十分艰巨。当时的情景是,许多学科领域的研究方向和研究工作需要恢复和建立,研究队伍青黄不接,研究经费相当匮乏,整体水平与国际先进水平的差距继续拉大。这种局面引起许多有责任感的科学家的忧虑。1981年,89位学部委员致函中央领导,建议借鉴科学发达国家的成功实践,设立面向全国基础研究的自然科学基金,充分发挥科学家在配置基础研究资源方面的作用。此议得到中央领导同志的首肯。从1982年起,中国科学院的科学基金开始实施。出于促成全国自然科学基金制度的建立,在此后一年多的时间里,我尽力收集了一些发达国家有关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机构的资料,提供给科学院的领导者们参考研究,并且多次向中央领导提出了有关建议。记得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成立前近一年的时候,在1985年7月3日和7月12日两次给小平先生的信中,我都提出了成立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的意见。1985年7月16日小平先生接见我时,我又向他面陈建立自然科学基金制度的重要性。我觉得,从吸引国外优秀华人科学家回国的角度看,那时在国外的许多人在今后十年、二十年,都会成为科技界的领袖。这是祖国的财产,要吸引他们回来,重要的办法之一,就是要加大对基础科研的投入。对国内的科学人才,要鼓励他们做创新性的工作,也要有基金的支持。为此,我建议尽快建立国家科学基金委员会,基金应该完全用在自然科学的基础科学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上,委员会必须要有浓厚的学术意识,必须有独立性,不能属于现有的任何国务院的行政机构。委员会负责人必须是第一流的科学家,对基础科学,应用基础科学有个人经验和全面了解。必须把权交给科学家,不是上面还有个行政机构来管。不然很难行使公正的评价。重视和加强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是一个长期的想法,方针不能老改变,要稳定下来。小平先生和其他在场的中央领导都明确表示,赞成成立这样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小平先生说,这是个新生事物,先干起来再说。此后不久,国务院便正式设立了管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机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
事情已经过去20年,但至今回想起来,我仍为小平先生等中央领导同志广纳进言的高风亮节所感动。
在这一时期,中国在科学技术管理体制方面发生了若干重大改革。自然科学基金制的实施和自然科学基金委的成立,无疑是其中意义极为重大、影响极为深远的事件。自然科学基金肩负支持基础科学研究的使命,系统地引入同行评议制度,坚持科学家自由选题,自由申请,平等竞争,择优支持。这一制度的建立,不仅为基础科学研究提供了稳定的经费来源,还有利于科学家在感兴趣的方面自由探索,激发科学家的首创精神;有利于名不见经传的青年科学人才脱颖而出。正因如此,从中国科学院科学基金开始实施起,基金制度便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全国自然科学基金的建立更给中国基础研究事业带来了勃勃生机。我十分高兴地看到科学基金制为推动中国科技体制改革所发挥的积极作用。
到了90年代初,中国现代化建设开展得蓬蓬勃勃,发展经济成为举国上下认同的硬道理。在发展科学技术方面也确定了“经济建设依靠科学技术,科学技术面向经济建设”的基本方针,后来又提出了“攀登科学高峰”的口号,围绕这一方针形成了“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试验开发”三个层次的总体布局。但是,在科学传统和科学基础本来就比较薄弱的中国,对基础研究的重要作用以及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和技术开发之间的关系,全社会在认识上难以形成共识,在实际上也难以对基础研究给予切实的重视和强有力的支持。以国家支持基础研究主渠道的自然科学基金为例,1992年,总经费仅有2.26亿人民币(按当时汇率约折合4000万美元),而当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一个物理系的研究经费就有800万美元。人均经费差距更大。国内科学基金支持的人均强度为3700元人民币(约折合684美元),哥伦比亚物理系人均研究经费则高达47万美元。然而,在这样困苦的情况下,自然科学基金坚持支持基础研究的方向不动摇,资助项目获得许多高水平的成果,在推动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等方面也作出了重要贡献。取得这样的成绩的确是令人钦佩的。1992年5月,恰好自然科学基金委举行科学基金实施10周年纪念活动,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了一个座谈会。记得不少优秀科学家出席了会议。时任中央书记处书记的温家宝先生也到会作了报告,高度评价了科学基金所取得的成绩。我荣幸地应邀参加了会议,并作了题为“没有今日的基础科学,就没有明日的科技应用”的演讲,分析基础研究的战略地位及其与应用研究、技术开发的关系,把基础研究比喻为“总机关”。“总机关”一动,下面的整体就要发动。呼吁加大对科学基金的投入,进一步发挥科学基金在发展基础研究方面的作用。
从1992年到现在,又过去了十多年。全社会对基础研究重要性的认识得到了很大提高,对基础研究的投入有了较大增加,研究环境不断改善。2005年,科学基金经费达到27亿元,约为1992年的12倍。在政府有力的支持下,经过自然科学基金委、国家有关部门和全国科学界的共同努力,中国基础研究的整体水平有了长足的进步,在一些学科领域,如人类基因组、纳米材料、全球变化、古生物等方面取得的不少成果,在国际同行中产生了重要影响。尤为可喜的是,基础研究队伍年龄结构不断优化,“青黄不接”的局面基本得到扭转,一大批优秀中青年学科带头人成为中坚力量。这些都为中国基础研究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很好的基础。
中国有句成语“未雨绸缪”,意思是凡事要加强预见性,提前作好准备。思考中国今后基础研究的发展和科学基金工作,有必要把握世界科学发展的走势。当今的科学,日新月异,异彩纷呈,正孕育和涌动着新一轮革命的浪潮。以物理学为例,对客观世界的探索与认识不断地向新的深度和广度拓展,从基本粒子的微观世界、纳米尺度的介观世界到星系的宇观世界,从飞秒瞬间到宇宙时标,从生命起源到人类的自我认识,构成一个又一个色彩斑斓的研究方向;在诸多领域涌现出现有知识理论体系所不能解释的实验现象和观测事实,包括暗物质、暗能量等,酿成物理学大厦上空的“一团乌云”。如果说历史上被称为20世纪物理科学大厦上空“两朵乌云”的黑体辐射谱的“紫外灾难”和光速不随运动参考系而变的实验,催生了量子论和相对论,形成人类新的时空观、运动观和物质观;那么对于目前这“一团乌云”的最终认识必将对整个自然科学、哲学乃至人类社会产生难以估量的影响。
去年4月15日,我在由中国科协、科技部等联合主办的世界物理年纪念大会上有一个讲话,提到宇宙总能量中,仅是约5%(由质子、中子、电子、原子核、原子、分子组成的物质)属于我们已知物质的能量,另外约25%为暗物质的能量,约70%为暗能量。暗物质对所有我们能测量的光、电场、磁场、强作用(核力场)都不起作用,可是它和引力场有作用,通过引力场我们能测量到暗物质的总能量比已知物质的总能量要大约5倍。
暗能量能产生一种负压力。最近几年,通过哈勃太空望远镜的观测发现,我们的宇宙不仅是在膨胀而且是在“加速地”膨胀。从膨胀的加速度可以推算出,宇宙是由于一种负压力,也就是暗能量的存在才膨胀的。我于2004年在《物理快报》(第21卷第6期)上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为“暗能量的可能来源”,表述了“天外有天”的观念,就是说,因为暗能量,我们的宇宙之外可能有更多的宇宙。另一篇是我最近发表在2005年 Nuclear Physics A 750, 1, 的文章名为《强相互作用夸克-胶子等离子体及未来物理学》(The strongly interacting quark-gluon plasma and future physics),试探和解释了最近美国高能核物理的新发现和暗能量的关系,提出了“核天相连”的观念。所谓“核天相连”,是指核能也许可以和宇宙中的暗能量相变相连。最近美国布鲁克海文国家实验室由极高能量的100GeV/核子金核与100GeV/核子金核对撞产生和发现的新的核物质。这种新的物质,我称它为sQGP(强相互作用夸克胶子等离子体)。这篇文章的目的是探索sQGP和暗能量的关系。可见,了解暗物质和暗能量将是21世纪科学面临的大挑战,也是对全世界年轻物理学家的大挑战。
去年是纪念爱因斯坦的世界物理年。一百年前一个迫切的科学之谜是太阳能的来源。那时候,所有地球上的能量均来自太阳。可是,太阳如何能似乎无尽地发光?如何能成为如此庞大的光源?这就引起20世纪初物理学家对光的研究。1900年德国理论物理学家普朗克(Planck)大胆地做了量子假设,写下了普朗克方程说明了物体在不同温度时,发出的光的能量是怎样分布的。但是,量子假设和经典力学的原理是矛盾的。1905年,爱因斯坦根据迈克尔逊-莫雷测量光速的实验结果提出了狭义相对论。因为有了普朗克方程的量子假设,1925年海森伯(Heisenberg)、薛定鄂(Shroedinger)、狄拉克(Dirac)、费米(Fermi)等就提出了量子力学和量子统计学。
从那时起,从狭义相对论和量子力学这些理论的应用,就产生了原子结构、分子物理、核能、激光、半导体、超导体、超级计算机等理论和应用。几乎20世纪相当大部分的科技文明,都是从狭义相对论、量子力学来的,都是从研究光速和地球旋转之间的关系、研究热的物体发出的光的光谱而来的。没有狭义相对论和量子力学,就没有今日的这些科技文明。19世纪的人很难想象我们的激光、半导体、超导体、超级计算机等应用。20世纪如果没有这些基础科学,就不会有20世纪的这些科技成果。
21世纪初我们面临的科学挑战,绝对是和一百年前我的老师和前辈们面临的科学挑战是同一级的。暗物质是什么?暗能量是否能被我们了解和掌握?21世纪的基础科学的成果将引起一大批的新科技观念和文明的革命。这些新科技的发明和应用也会是20世纪的人类很难想象的。
新一轮科学革命,对于人类和世界各国一样,既是一个挑战,也是一个机遇。“机遇只垂青于有准备之人”。面对即将到来的科学革命的挑战,许多国家纷纷制定对策,包括调整科技发展战略,确A优先领域,加大对基础研究的投入等。据我所知,美国国会已通过了在未来5年内实现科学基金会经费翻一番的动议。对于中国而言,由于种种原因,我们曾丧失了20世纪大半世纪科技发展的很多历史机遇,现在一定不能再错过。尽管我们的基础研究整体水平还不是最高,但完全可以在某些学科领域取得“点”上的突破,并以此带动全面的发展与提升。我们应该树立这样的信心。同时要采取有力的保障措施。其中重要的是政府继续增加对基础研究的投入,使其占全国用于研究与发展(R&D)的总支出中的比例从现在的5%左右逐步提高到15%以上,同时进一步发挥自然科学基金的作用。自然科学基金委也应发扬光大良好的工作传统,珍惜已经获得的崇高声誉,发挥引领未来的作用,义无反顾地肩负起迎接新一轮科学革命挑战的神圣使命。
我们中华民族不乏聪明睿智。我们的祖先曾以辉煌的科技成就影响和推动了全人类的文明进步。只要我们抓住机遇,埋头苦干,中华科技伟大复兴的目标就一定能够实现。 |